潘伯鹰书法:墨成池,胸臆淋漓


一 博雅尚古的文艺开端
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成名的一代书法家基本上都能以“文人书家”称之,潘伯鹰则可谓此中典型。潘伯鹰(一九〇五—一九六六)原籍安徽怀宁,出生于安庆。其父潘雨林虽非巨宦,却雅好翰墨,家中所藏书画使幼年的潘伯鹰濡染寖馈,其敏慧心性得到极早开发。潘雨林于民国改元之后在北京任职,又使潘伯鹰在少年时期往返就读于安庆与北京之间,旅途风尘,激发少年心绪,培植艺文萌芽。潘伯鹰童蒙初开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文化、人心、风俗均遭遇千年巨变。家学濡染,使得潘伯鹰在诗词、书法方面早慧于人,而新文化对新生代的影响,也使得他崇尚个性发展,不甘于按部就班进入生活藩篱。比较潘伯鹰一生诸多文化建树,诗词、书法是其终身不曾离开的素业,而最初使他大获赞佩、驰誉名场的,却是小说,而且是长篇小说。诸多投身文坛者多年甚至终身的梦想,在潘伯鹰二十岁出头时便实现了。蜚声载誉之际,潘伯鹰却又离开小说坛坫,将主要心力贯注于书法。这在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中是一个鲜见的特例。不论潘伯鹰的道路选择是否最终落入钱锺书曾经自嘲的“半间不架”,但自己设计文化生命并一生贯注,却是潘伯鹰独特难能之处。潘伯鹰曾经对好友吴兆璜说:“吾以十年潜心于学,以十年致力于小说。是书成,吾不复知有古人。”潘氏于小说创作之自信可见。长篇小说《人海微澜》是潘伯鹰“十年潜心于学”之后的结晶,而在此小说中,也对书法多有言及,潘伯鹰借书中人物之口,谈到王献之《洛神赋》的“神韵”,也谈到“侧锋取姿的是王梦楼”,“骨力劲挺的还是王梦楼”。在人物对话中议论魏碑的“磔笔”之妙以及《乙瑛碑》当时的行市。《玄隐庐诗》还收录了潘伯鹰少年时期的学书感悟:“客舍低头写万纸,苦学来禽与青李。”可见王羲之《十七帖》早成日课。凡此,可见二十岁之前的潘伯鹰“潜心于学”,所骛多方,在书法方面亦非浅嗜初尝。中国书法的源流发展及民国初年的书坛状态于潘伯鹰已然领略条贯,这为其以后在诸多文艺门类的游弋中终以书法为归宿奠定了基础。潘伯鹰的书法道路,与现代诸多文人书法家既有重合,又自具特色。寻绎其中,中国书法在二十世纪经历的由漫漶向专精转化,书法家由自然生成到规范养成的转化,脉络清晰,堪为镜鉴。

行书《临李仕倜书》
二 碑帖争持中的孤诣独行
一九一六年,十一岁的潘伯鹰随父第二次居家北京。十多年间,他在这里读完中学、大学,开始职业生涯,也进入文化生涯。在就读新式中学之际,父亲引潘伯鹰投拜于当时京都名士吴闿生门下。吴老师号北江先生,为晚清大儒吴汝纶哲嗣,秉绪先业,以经学立身,又是著名诗人、书法家。与潘伯鹰先后就教吴门者,还有齐燕铭、贺孔才、曾克耑等,以后均成为学者型书法家。师友濡染、环境熏陶,使当年的潘伯鹰俨然“京派”。吴闿生书法,以颜真卿宽博凝重体态植基,又得苏东坡波磔意态,这是清代翁方纲以来诸多士人的书法常态,也影响到潘伯鹰。潘伯鹰早年书作《波外楼近体诗钞册》,是对前辈诗人乔大壮诗作的抄录。纯然行书,甚少草意,间架颇见颜真卿之端严,波挑时显苏东坡之倜傥。在得窥书法门径的最初阶段,潘伯鹰对颜真卿与苏东坡的书法格外垂青。颜真卿是唐代书家承续王羲之的典型,其厚重气息又不同于六朝绮丽。苏东坡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全才,经史文章、诗词书画,独步当时,凌烁千秋,又兼一生遭际坎坷终不失意趣,自适自奋而激励后学。潘伯鹰书法道路的开启,即遵循苏东坡“论书当观其全人”的意旨,在其六十一年的生命中不绝如缕地绽放着文艺创造的似锦繁华。“颜意而苏味”即成为潘伯鹰一生书迹之基本形态。

《颜勤礼碑》(局部)
北京求学期间,潘伯鹰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琉璃厂、海王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一九二二年一经出土,潘伯鹰立即在琉璃厂的“问古斋”看到了拓本。当时潘伯鹰家住麻线胡同,梁启超家住南池子。为两家装裱碑帖的“仿古斋”伙计与潘伯鹰交好,为梁启超送碑帖时每先往潘家。潘伯鹰回忆说:“所以梁氏所藏碑帖,我多已得快先睹了。”潘伯鹰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附中和北京市第一中学就读,显然因为兴趣偏重于中国古典,诗词文章及书法均超越时辈,但他的数学与外语成绩均很不好,先是被高师附中退学,后又影响到报考大学。以后与潘伯鹰成为文友的钱锺书,也是偏科的奇才,但潘伯鹰远不如钱锺书能够得到罗家伦那样既有眼光又有权力的大学校长的青睐,他中学毕业之后为补考外语竟焦虑致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疗治。也就是在此百无聊赖之中,书法颐养了潘伯鹰的身心,也使得他对中国书法源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民国初期的书坛,被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诸人宣扬的“扬碑抑帖”风气笼罩,在比较之中,潘伯鹰没有致力于康有为竭力宣扬的魏碑,而是将心绪投入到更加古老、更加具有古典性质的汉碑,在三年养病之中,临写汉碑十几种。显然,汉碑的宽博典重,适宜于庙堂隆范之书,而潘伯鹰以心性趣味贯注于韵语翰藻,已然在颜真卿、苏东坡秉绪的王羲之流脉中自得其乐。面对父辈师长耳提面命必须顶礼膜拜的皇皇汉碑,竟难入佳境,这使潘伯鹰困惑回惶。纯粹帖学,当时被目为穷途末路,而要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书法楷模,又遭遇瓶颈般的道路障碍。潘伯鹰不得不以中庸思路折中而在既为王羲之流脉,又被碑学理论列入北派典型的褚遂良沉潜。在反复临写褚遂良的代表作《倪宽赞》《房梁公碑》《大字阴符经》后,大得意趣,潘伯鹰找到了一条不囿南北书派、避免理论困惑与心理自惑的书法道路。

临《大字阴符经》(局部)
三 盛名之下的书法沉潜
潘伯鹰到北京之后,恰是“五四”运动酝酿爆发之期,一切“旧学”,均受到冲决扬弃。潘伯鹰所热衷的古文诗词书法之类,在新时代已经难为谋生之具,求学谋职的人生压力,又使他不能不在惶惑与病羸中报考大学。潘伯鹰于一九二四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并未能进入技术系科,而是在铁道管理学院就读。也就是在大学期间,潘伯鹰继续着自己的书法诗词素业,其长篇小说《人海微澜》也在《大公报》连载后出版发行,一时轰动文坛。当时,以茅盾、巴金等人为代表的新小说风靡长久,同时又有张恨水为代表的市井言情小说分庭抗礼。潘伯鹰的小说,既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又秉绪《红楼梦》的传统风格,得到了当时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宓的揄扬。吴宓是一位曾经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外国文学专家,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十分有别于当时诸多新文化学者的认识。他主张来源于中国古典“六艺”的“博雅”观念,对于潘伯鹰小说中体现的种种饱含中国社会文化因素的人情世相十分欣赏,并将其推荐为大学生必读书。当时,钱锺书的《围城》还远未产生。可以说,在揄扬钱锺书之前,潘伯鹰是吴宓最先青睐的文学天才。此后,“雨僧”与“凫公”的文学交情一直延续到晚年。吴宓居处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还将青年教师徐永年介绍给远在上海的潘伯鹰,使得这位尚在探求书法道路的后进得到教益。《人海微澜》之后,潘伯鹰一鼓作气,创作出版了多部小说,并有作品被著名导演郑正秋搬上银幕,由胡蝶主演。可以说,青年时期的潘伯鹰,已经居于中国文坛不可忽略的位置。但即使名声如此,潘伯鹰并未进入作家团体从事专业创作。显然,他所愿想的生活,是一种不受羁绊而尽兴发挥才华的“博雅”状态,不在任何局囿中作茧自缚,又对从心底生发的热爱物事竭力探寻,这样宽博而深厚的文化履迹,从他终身服膺的苏东坡和先后师事的吴北江、章行严身上都可以窥见。

临《丧乱帖》
潘伯鹰一九二五年大学毕业之际,在铁路系统就业,因小说及诗书才华,结交多为当时文坛名家。辛亥革命元老、后主办成为传统文化重镇《甲寅》的章士钊,将夫人吴弱男的义女何世珍介绍与潘为妻;叶恭绰将自己收藏的敦煌经卷慷慨赠予;唐醉石屡为刻制“岁星楼”“隋经室”印章。凡此种种,其背负狂名也有以。但从潘伯鹰一生作品及言论来看,他实际上是十分理性之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信条乃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执端用中”,总在追求正确,追求公允,并且“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在书法实践中不断体会,也不断进行理论思考,逐渐对阮元以来一些风靡书坛甚久的理论发生怀疑,在对片面张扬“碑学”的反诘中形成了自己的书学理念,也形成他不断变化、不断深入、也不断淡定的书法形态。他以“二王”风范为皈依,遂对“二王”系统的历代名家深入研寻,其书法表现,也与其书学研究同步发展。因为“二王”真迹的湮灭难藉,初唐时期对“二王”书系的传续脉络即成为必须厘清的学术问题。在理论上,潘伯鹰不赞同阮元的“南北书派论”,阮元将欧阳询、褚遂良归为“北派”,从而否定欧、褚为王羲之传人。潘伯鹰少年时期即从家学及吴闿生濡染的颜真卿书法上溯,皈依“二王”,而作为颜真卿直接师承的褚遂良,若与“二王”分离,书史这一脉络岂不是断裂了?潘伯鹰对褚遂良书法的用笔进行了长期细微琢磨分析,他后来总结说:“右军隶法,含在笔内,在字形上不太显著。而遂良则是抓住了这一要点,尽量将他发挥显明出来的。他传下的碑,无论《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或《伊阙佛龛记》,都是直下明白的隶书根基,使人一见分晓便知来历。”潘伯鹰从褚书对王羲之“隶意”进行吸纳,亦分辨了从六朝到隋唐的书法演变。在清末以来“碑学”思想弥漫之际,片面激烈的皮相之论充斥书坛,潘伯鹰既不认同,也没有沦入针尖对麦芒的意气相争,而是在具体问题上申明己见,厘清书法史上一些被淆乱的片段。他说:

临《房梁公碑》
初唐虞、欧、褚、薛四大家之中,虞是智永禅师的弟子。智永无论就血缘或就书法,皆是王羲之的后裔。欧则父子二人都是从隶法来的,而欧阳询的定武《兰亭》,尤其传右军的书脉。褚是专门学右军的,他又受法于虞、欧两位前辈。薛稷是魏徵的外孙,他专学魏家所藏的虞、褚真迹,尤其努力学褚,得其神貌。这四大家无疑是属于王右军系统的。……自从王羲之精于隶法,独成新派之后,中国书法的传统已与他分不开了。唐太宗时最大的书家,虞、欧、褚、薛无不从王氏得法。自颜、柳以至“宋四家”,也全是以王氏为旨归。自赵孟以至董其昌更是明白地有志承继王氏。即使清朝以来,书法衰歇,但凡是学书者也无不拱王氏为北辰。所以尽管各时代的特色不同,而其中自有一条无形的线,将其连接起来,成为一贯相承的脉络。

行书 《论兰亭》扇面
潘伯鹰这些论述,明确认为唐初四大家书法皆传续“二王”,与阮元等所论不同。隋唐书法的直接秉绪究竟是北朝以魏碑为代表之碑刻书风,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帖札书脉,为争执未休的历史迷局。潘伯鹰之说自然有其帖学中心因素,但南北朝时期书法的主要传续为“二王”系统,北碑尚未受到书家重视,因而也难以成为承续楷模,应该是历史真实。
潘伯鹰家境优渥,性情倜傥,才华横溢,少年成名,“脱略小时辈,结交尽老苍”。如果仅仅把他视为一个悠游书翰,驰驱名场的风雅名士,即成皮相观人。他对文化艺术充满探寻精神,对人生社会寄予理想热情,而又经常反思,自惕自勉。这是潘伯鹰从苏东坡及章士钊得来的处世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宽博深邃,但又不趋向极致。书法之外,他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女挽车行》《拾煤核》是潘伯鹰青年时期诗作中的古风长句,诗中流溢着屈原、杜甫、白居易以来“哀民生之多艰”的炽热情怀。潘伯鹰最终并未成为政治人物,他的兴趣及认识,始终将自己定位于诗翰笔墨之兴趣追求,而他的书法及诗歌,也伴随其生命恒久。

行草毛泽东《浪淘沙》
四 服膺沈尹默重振帖学——山城岁月的翰墨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诸多文化人聚集于此。潘伯鹰以孔祥熙秘书之身份,得以在中央银行谋一业余时间充裕之职务。他将大量余闲用于诗歌书法之雅集活动。以元老江庸牵头挂名而成立的“吟河诗社”,即成为当时诗人和书法家的聚会之所。当时参与“吟河诗社”的诗人,其中若章士钊、叶恭绰、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乔大壮、高二适、谢稚柳、蒋维崧、王蘧常、潘受、郭绍虞、沙孟海、曾克耑、许伯建诸人,均是诗人型书法家,也均在二十世纪中国书坛发生不同作用及影响。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在论争中分庭抗礼,甚至分道扬镳。到得抗战军兴,外敌侵凌,使得民族传统文化在不甘屈服的人们心中更显珍贵高华。即以诗歌而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诗社活动之频繁超过了晚清以来的任何时期,与旧体诗词最为密切的书法染翰,也在重庆表现得空前活跃。当时年未届不惑的潘伯鹰,缘时际会,成为诗词与书法两种传统文化活动的中心人物。十四年抗战时期,潘伯鹰于书法探寻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在对沈尹默的请益交流中明确了对王羲之书法流脉的继承发扬,此后即为恢复“帖学”不遗余力。这也是抗战胜利,复员东归之后,沈尹默、潘伯鹰等人在上海张扬“帖学”,形成新的“海派”书群的重要酝酿准备。在此之前,以于右任为代表的碑派书法,早已蜚声书坛。而于右任有巨擘之名位,无独裁之痼弊,对张扬帖学最力之沈尹默毫无扞格,反而给予极高评价,说沈尹默是书法科班,而自己只是玩票。也正是在这样宽博的学术气氛之下,沈尹默与潘伯鹰等人恢复帖学的努力,作为书法发展的一种自然现象,在上海书坛最先得到倡扬与追随。这既有艺术风格“各领风骚”的内在理路,也离不开具体人物的不懈努力。潘伯鹰在其中的作为,十分明显。他撰写了一系列论述王羲之书法流脉传续的文章,自己也反复临摹其中的古贤遗墨。褚遂良、苏东坡之外,他对孙过庭、杨凝式、李建中、蔡襄、黄庭坚、米芾,乃至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等帖札书法名家均深入研寻,体察其不同特色,辨证王羲之书系的发展幽微。其中,尤以对赵孟的论述,最具心眼。多年来,赵孟在书坛久受诟病,所谓“帖学大坏”,颇多归咎于松雪翁。但潘伯鹰说:
“二王”这一系统的笔法在宋朝受了挫,到元朝才又恢复。这一恢复的力量几乎是赵孟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书法在宋朝,不论是由于米芾那样力言古代变法的旧派,抑或由于黄庭坚那样暗用古法的新派,都把晋唐的面目神情改变了。这样愈改愈远,到元朝却又改回头来,复兴了古法。
有志学书的朋友,应该用赵所用的方法去学古人。因为他的方法是最正确的方法,学习古人久了,再来反观赵字,自然更容易领会到他的好处……这时候就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极伟大的书家,我们已经知道董其昌是到了七八十岁才这样承认了的。

《行书合集长卷》(局部)
曾经久背骂名的赵孟,其实是传续“二王”的功臣。在潘伯鹰眼中,赵孟是以保守面目完成了书法革新的事业。潘伯鹰的这种看法,与他毕生的文化认识和艺术实践有关。他多年服膺的师尊吴闿生、吴宓、章士钊,在文化上都有“保守”之名,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侃切知见,在经历多年误解之后,终于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复苏之中得到重新评价。
潘伯鹰的书法实践,与其平生“博雅”崇尚知行合一。从潘伯鹰遗留墨迹可见,除王羲之之外,他临摹最多的是赵孟:仅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即有《自摹赵孟二赞二诗》、临赵孟《书苏轼诗》《草书千字文》《太湖石赞卷》《行书三札》等。同为海上名家,同在倡扬帖学阵容,潘伯鹰与沈尹默、白蕉对赵孟的认识颇见不同。沈尹默明确表示学习“二王”不能以赵孟为门径,白蕉也以为赵孟书法不足为法,也正是在各抒己见之中,书法学术得到深入拓展,书史幽微得到充分发撷。与海上诸家相较,潘伯鹰崇尚并且临摹的古人名迹最广泛,就书家个人风格而言,这可能显得芜杂,甚至导致潘伯鹰最终书法面目不够独特显豁,但在恢复“二王”流脉的时代性努力中,潘伯鹰堂庑广大,意态恢宏,不断将个人研习与书史研寻结合沉潜,反复体验,其传续价值不当漠视。

临《褚遂良圣教序》
五 不甘止步的晚年精进
纵观潘伯鹰平生书翰,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所作最多。这十来年间,潘伯鹰处境平静,使得他能够在正常心绪中致力于所衷事业。他先后在同济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任文学教授,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文坛健将,渐渐处于社会文化边缘,而对于书法的热爱研寻,潘伯鹰却更加执着精勤。当时,书坛一片冷寂。潘伯鹰以昔年著名作家之身潜心书法,为许多人难以理解。在一九五九年致许伯建札中,潘伯鹰袒露了自己的心曲:
鹰少好涂鸦,老而不悛,此乃兄之所知也。十载以来,此习益甚,虽颠沛仓遽,劳倦饥乏,亦且展纸研墨而为之。当幽忧愤悱之际,亦颇赖此自遣。惟此事今日益不为人所重,甚且加以嗤点,而弟则转以此得杜门放意而为之。自趋公学习之余,无间寒暑,晨夕殆皆费日力于斯矣。窃于昔贤用笔之意与其所以寄其心志者,未尝无所会也,尤不自惴。以谓此虽小道不足言学,然在今日,实亦为绝学矣。今我不述,后生何闻。纵不敢以此自夸,要不为一时之盛衰所移,故亦为之而不悔也。

《百篇千里》七言联
“用笔”与“意兴”之融合,“小道”与“绝学”之关联,在那样一个喧嚣而空泛的文化环境里,在一生追求文化创造、追求笔墨趣味,也追求心绪安宁的潘伯鹰心中、手下,得到体验和升华。也就是在这样的坚守和努力下,迎来了书法艺术的一片晴空。一九六一年成立的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由沈尹默任主委,潘伯鹰与郭绍虞、王个簃为副主委。这个经过多年努力才得以问世的海上书法团体,使得潘伯鹰热情顿发,必欲大有作为,当年在重庆主持“吟河诗社”的雅韵深衷重新氤氲心际。潘伯鹰与白蕉、潘学固等人,积极配合沈尹默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青年文化宫开办书法培训班、讲习班,一方面培养若干年来几乎断绝的书法人才,同时也“教学相长”,温习整理各自的书法理论。这段时期,潘伯鹰不断总结自己一生的书法研习轨迹,张扬帖学,也警惕偏颇,更向昔年未多涉及的章草浸馈。可惜凫公折翼,一九六三年之后即染绝症,辗转床榻,未能尽展长才。一九六五年“兰亭论辨”发生时,敏锐感觉此举为对传统文化扫庭犁穴的是历史老人章士钊,而与章士钊关系最为密切的书法家乃潘伯鹰,且潘伯鹰历来对“扬碑抑帖”之说所持明确反对之言论文字,也为章士钊所熟知。但此际潘伯鹰已然卧病难起,抗辩郭沫若诸人的历史责任于是由当时并不知名的高二适承担。因“兰亭论辨”,促成了王羲之书法流脉的重新发扬,可惜,一生服膺“二王”的潘伯鹰未能得见。潘伯鹰逝世于一九六六年五月,时年六十一岁,比起他服膺的古贤颜真卿、苏东坡都要年轻,实为天损长才;但未如年龄相近的白蕉,此后几年受尽磨难。“行其所当行,止其不得不止。”作为苏东坡的千秋知音与私淑弟子,潘伯鹰也算有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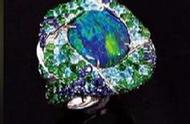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22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22号